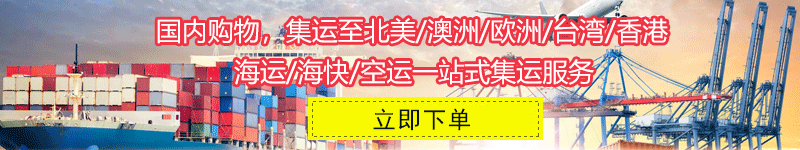近日,《国家宝藏》刷爆了朋友圈,将宋朝大美河山浓缩成一幅金碧青绿山水的《千里江山图》、集瓷器大成的“瓷母”各种釉彩大瓶、记载了千年文脉的“石鼓”、周代礼乐制度的代表曾侯乙编钟……文物背后前世今生的故事无不让人津津乐道。
不过,除了这些国宝,不少拥有极高艺术、历史价值的中国文物在战火硝烟里、在时代变迁中流离失所,散落在海外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
这篇文章无意一一列举所有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目的也并非简单谴责当时偷盗者和文物贩卖者的行径,更不会因为这些文物在动荡战火中幸存下来而赞颂这种行为。我们只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挑选几家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和他们的藏品,让大家不要忘记还有这些中国文物漂流异乡。如果在旅行中经过,不要忘记去探望一下“没能回家”的它们。
一、北美篇
1、弗利尔美术馆与《洛神赋图》:《洛神赋图》的“异地恋”
还记得2015年秋天故宫博物院超高人气的《石渠宝笈特展》吗?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武英殿的明星,那么延禧宫中的领衔者就非宋代摹本《洛神赋图》莫属了。在《国家宝藏》中,传说辽宁博物馆推荐的三件国宝中也有《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可见这幅画的重要性。
《洛神赋图》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由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绘,他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爱,最后因人神殊途而怅然分别”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分别时,曹植在仆役的陪同下站在岸边,洛神隔着洛水含情脉脉回望,若往若还,依依不舍。
但你知道吗,这幅画还有兄弟姐妹,其中唯一一幅宋朝白描摹本位于遥远的大洋彼岸——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不过遗憾的是,根据博物馆捐赠者弗利尔的要求,他的藏品不能出售,也不能出借给其他任何地方。所以,它与中国摹本,只能如曹植与洛神一般无奈地隔水相望,“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
也正因如此,对于中国旅行者来说,弗利尔美术馆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世界上收藏有最好中国文物的海外博物馆之一。
它的建立要从西方人对于东方艺术的痴迷说起。早在17世纪末起,西方就刮起了一股东方风,拥有中国瓷器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深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一些人甚至“疯狂”地将自己的家装饰成所谓的东方异域风,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创作的《孔雀屋》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
这件作品正收藏在弗利尔美术馆。这本是一间餐厅,墙壁四周装饰的孔雀金色屏风仿佛出自日本“琳派”画家之手,其间摆满了各种青花瓷器。中间是惠斯勒创作的《瓷国公主》,一位西方面孔的女孩身着和服,手持团扇。
在这些追逐东方艺术的收藏家中,不得不提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正是他一手建立了美术馆收藏。
他有一句经典的豪言壮语:“元代以后的画不用拿给我看。”一方面可见他的收藏趣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藏品之精,年代之久远,连明清时期的绘画、雕塑、工艺品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不同于一般收藏家仅是从欧美古董商手中直接购买东方艺术品,他曾四次亲自前往东亚拜访收藏家、古董商,收集藏品,探访龙门石窟等古迹。这段时间(1895-1922年)正值清朝末期,社会动荡,危险重重。
这段经历大大丰富了弗利尔的收藏,他在北京寻找唐、宋及元代早期绘画时曾经说过:“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6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10倍于那个数字。”
20世纪初,弗利尔萌生了“将藏品捐赠给美国政府、建立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最终在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下实现,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
捐献藏品达一万五千多件,包括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远东艺术品、印度和中东文物、古埃及艺术品以及包含“孔雀屋”在内的美国艺术家作品。
美术馆不仅拥有全美最多、最精彩的中国绘画藏品,青铜器、玉器、佛教造像收藏也相当精彩。只可惜,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再也无缘“回家”,我们只能在华盛顿一睹它们的风采了。
【其他重要中国藏品】
弗利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2、波士顿美术馆与《历代帝王图》:与中国画初结缘
在美国,与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绘画收藏相比肩的恐怕就要数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了,这也是美国最早收藏中国画的艺术机构之一。
在中西交流尚不通畅的时候,西方人很难欣赏审美情趣差异巨大的中国卷轴画:画景没有透视,画人不按解剖学,这怎么能叫做好画嘛!甚至有西方媒体曾经评论中国画“单调,没有条理,色彩已褪,令人乏味。”
但在波士顿却有一群拥有慧眼的人,发现了中国绘画之美,他们是美术馆东方艺术研究院欧恩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美术馆赞助人邓曼·罗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美术馆建立日本和中国收藏至关重要的人物冈仓天心。
不同于美国其他城市,日本文化在这里十分盛行,交流也相当频繁,因此最初很多中国绘画是从日本人手中购得的。
比如1895年,中国南宋绘画《五百罗汉图》展的作品就来自京都大德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的中国绘画展。展览结束后,寺院将10幅《罗汉图》出售给邓曼·罗斯,成为波士顿美术馆最早一批中国绘画收藏。
唐代宫廷画师阎立本所做的《历代帝王图》也是邓曼·罗斯通过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买下的。这幅画还被称为《古帝王图》、《十三帝图》等,绢本设色长卷,描绘了历史上的十三位中国帝王。
他们分别是:前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南陈文帝陈蒨、南陈废帝陈伯宗、南陈宣帝陈顼、南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
阎立本通过人物五官表情的细腻刻画,对各位帝王的功过得失一一评价,笔墨间可见褒贬。
费诺罗萨和邓曼·罗斯之外,前者的学生冈仓天心又陆续征集了不少高品质的、名气很大的中国古画,如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夏圭《风雨行舟图》、陈容《九龙图》等。现在波士顿美术馆共收藏宋、元绘画213件,数量位列全美第一。
【其他重要中国藏品】
波士顿美术馆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注意事项:
中国传统书画对保存环境的光线、温度、湿度等条件要求很高,尤其是长时间的光照会使颜料褪色,平摊的展陈方式也会使纸绢受损,因此多数时间它们都保存在博物馆的仓库中,每隔几年才会拿出来展出,多现身在特展。因此,如果平时前往上述博物馆、美术馆,很可能见不到这些珍贵的古代书画收藏。
3、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皇帝礼佛图》:中国的“埃尔金大理石雕”
19世纪初,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埃尔金勋爵终于压制不住拥有雅典巴特农神庙石雕的贪欲,将一块块精美浮雕取下,切割成块,运回英国。这些文物被后人称为“埃尔金大理石雕”,存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有一块来自中国的佛教浮雕作品——《皇帝礼佛图》,无论是身世经历,还是艺术价值,都可与那件雅典的作品一较高下,博物馆馆长阿兰·普利斯特(Alan Priest)赞颂它是“中国的埃尔金大理石雕”。
它与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本位于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山西大同迁都至河南洛阳,崇尚佛法的他命人在伊水河畔的山崖间开凿石窟,工程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等数个朝代,绵延400多年。总计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
宾阳洞是其中最重要的洞窟之一,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文昭皇太后歌功颂德所建。宾阳中洞中间是一座释迦牟尼坐像,除了两侧侍立的菩萨、弟子像,墙壁上还装饰着浮雕,其中最精美的就是流落海外的《帝后礼佛图》。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在大臣、侍女的陪同下礼佛,人物线条刻画细腻,栩栩如生。
最初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美国收藏家弗利尔陆续到达龙门石窟,考察、拍照、拓片、测绘,之后将石窟介绍给西方。
然而这些本应作为研究材料的照片却引来了无耻之徒的觊觎,刺激了佛像的掠夺与盗卖。甚至有的人会拿着照片向买家展示,“预订”这些作品。兰登·华尔纳曾经讲述过当时的情景:仅在龙门石窟外就有1000名盗贼,军队每晚出动维持治安,经常有激战发生。
当时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的普埃伦对《帝后礼佛图》志在必得,1934年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老板岳彬签订合同购买这两幅雕像。岳彬联合土匪绑架了石匠,逼迫他们在夜色中将浮雕一块块敲掉,运至北京后转往美国,经过在中、美两地的多次拼接复原后,最终陈列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不过这件事并未划上句号,恶人终有恶报。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来自著名雕刻家刘开渠等十人的联名举报信,检举岳彬倒卖文物,检察院随后在他的家中发现了《帝后礼佛图》的部分残片。岳彬以倒卖文物罪判处缓期死刑,在狱中度过余生。
相比《皇帝礼佛图》,《文昭皇后礼佛图》的命运更加坎坷。一开始它并没有修复成功,浮雕残片失散在茫茫人海中。五年间,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的馆长希克曼四处寻找、收集这些遗失的碎块,之后按照礼佛图拓片,将它们和从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来的残片一点点地拼起来,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看到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也仅是完整浮雕的三分之二,其余的部分或在岳彬家被查获、收入龙门石窟库房,或已不知漂泊到何处了。
【其他重要中国藏品】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4、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与“昭陵六骏”:谁牵走了唐太宗的骏马?
当我们进入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雕塑馆时,你一定会被“昭陵六骏”震撼到:六匹骏马排开,占据了面对正门的一整面墙,射灯将它们依次照亮。
它们是唐太宗生前的爱马,分别是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
平定天下后,太宗曾经下诏:“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于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盖之义。”于是,传说阎立本奉命设计了六骏的浮雕草稿,之后交由工匠雕刻,安放在昭陵内,宣传太宗一生的丰功伟绩。
其中最生动的两幅是“飒露紫”与“拳毛騧”,不过遗憾的是,碑林中的这两件是复制品,原作收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飒露紫”选取了最经典的一幕——丘行恭拔箭。征讨洛阳时,唐太宗骑的正是飒露紫。战马在激战里放箭,将军丘行恭及时赶来,将自己的马让给了李世民,并为飒露紫拔箭。英勇的马儿后来竟站了起来,咆哮着作前进状,吓得敌人连连后退,解除了一场危机。
“拳毛騧”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形象,周身旋毛的黑嘴黄马。它也战功赫赫,据说在沙场连中九箭却依然顽强作战,直到胜利。
这两件文物流出的过程众说纷纭。据《国宝档案》所述,当时袁世凯已复辟帝制,让儿子袁克文负责兴建花园,并希望在里面放置一件“镇园之宝”。在古玩商人赵鹤舫的提议下,袁克文看上了“飒露紫”和“拳毛騧”,联合陕西督军陆建章和美国人毕士博盗墓窃取雕像。但是,狡猾的赵鹤舫并没有将原作交出,而是狸猫换太子,偷偷命人仿制了两件作为替代,原作后来卖给了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卢芹斋。
还有版本说,赵鹤舫买通袁克文,得到袁家运送货物的专用批条,顺利将浮雕运出;也有人说,飒露紫和拳毛騧是在袁世凯去世后才流出的。
无论过程如何,最终宾夕法尼亚大学答应了卢芹斋18万美元的开价(实际成交价格为12.5万美元)。不过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博物馆一时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先将唐高宗的两匹骏马“借到”博物馆,直到1920年底收到一笔20万捐款后才正式收入馆中。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5、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与荫余堂(Peabody Essex Museum):拆迁潮中的“幸运儿
最后我们将要介绍的这件展品有些特殊,它不是绘画、雕塑、陶瓷等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到达美国的过程也无关于盗窃、抢掠、交易,相反可以算是一次感人的“异乡重生”。
走进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你会惊诧地发现这里竟然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徽派建筑,甚至连室内陈设还保留着原主人的生活痕迹。博物馆工作人员确实把现实中的徽派老宅“搬进”了博物馆,这也是首座运至美国的中国本土完整住宅。
博物馆所在的美国塞勒姆小城与东方缘分颇深,她是一座港口城市,200多年前从美国启程前往中国的第一条商船正是从这里出发。博物馆共保存了22处历史建筑,东方部虽然也收藏了来自东方的各类文物,但以建筑艺术的相关书籍文献最为闻名,其中有些甚至是孤本。
时任博物馆东方艺术主管的白灵安(Nancy Berliner)曾经前往中国安徽旅游,她对当地古村中的粉墙黛瓦印象深刻,就此萌生了让美国人见识徽派建筑之美的想法,希望将一座真正的当地建筑搬进博物馆。不过由于文物保护的限制,他们只能考虑普通的民居。
1996年她和助手深入安徽大大小小的村落进行考察,无意间在休宁县黄村发现了超过200年历史的荫余堂。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高墙深宅,共2层,16间卧室,天井、鱼池、格窗、马头墙等元素应有尽有。当时房屋因缺乏修缮,仿佛随时就会倒塌似的,然而破败之间却掩不住原先的精巧。
更巧的是,这里的主人——黄姓富商后人正准备出售这座老宅,于是白灵安决定买下,迁移、收藏在美国的博物馆。
拆迁复原工程从1997年开始,共持续了6年。一块块砖瓦、一根根木梁被依次小心拆下,并仔细记下它们的具体位置。根据工作人员的统计,最后共有10000多块砖、50000多块瓦和2735件木结构,甚至连屋内的家具、陈设甚至生活用品也保留了下来。
经过两个月的海上漂泊,这些建筑部件抵达美国,在中美专家、工匠的共同努力下复原工程顺利完成。
现在荫余堂已经成为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展厅中播放的《荫余堂》纪录片向大家讲述着这座建筑千里迢迢到达美国的全过程。
而当年其他五座被看中的候选民居中,除了一座被美国一家基金会出资买下,异地重建外,剩下四座的原址上已经盖起了现代化的新式建筑。
对比它们的命运,荫余堂无疑是幸运的。这个项目不仅挽救了一座建筑的生命,它的意义或许还在于试图唤醒我们对古建筑之美,特别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民居的重新关注。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Peabody Essex Museum
6、北美其他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博物馆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Fogg Museum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亚洲协会及其博物馆(纽约)Asia Society and Museum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 Field Museum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Seattle Art Museum
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二、日本篇
今年春晚有一个特殊的环节,明代中后期的青绿山水手卷《丝路山水地图》亮相舞台。这幅地图也名为《蒙古山水地图》,包括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麦加)的广阔地域。
这幅画在去年年底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之前,曾经被日本近江富商藤井善助买下,收藏在日本藤井有邻馆大约80年之久。
其实,不只藤井善助致力于收藏中国器物、书画。由于政治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原因,日本建立中国收藏的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拥有中国文物最多的外国国家之一,而且藏品质量丝毫不逊于英、法、美等欧美国家。
1、中国文物进入日本的主要过程
中日文化艺术交流源远流长,已有上千年历史。根据史料记载,传往日本的最早艺术品是一方《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1782年由九州福冈县志贺岛上的一位渔民意外发现,现被列为日本国宝。根据印章风格和上面的“汉”字,可以推测这枚金印制于东汉时期。
(1)隋唐时期
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是在隋唐时期,尤其是盛唐先进发达的经济、科技、文化让邻国钦慕不已,争相仿效学习。从仿照唐朝长安城修建的奈良平城京和京都平安京,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之大。
7世纪起,日本圣德太子开始派遣访隋使,起初人数很少,通常只有十数人或数十人,但队伍中已经包括了留学僧和留学生。到了唐朝,遣唐使的队伍扩大了许多,尤其是在702年到752年之间使团人数经常多达四五百人。他们不仅在中国学习先进的社会制度、文化、佛法,归国时还将大量器具、造像、书籍等带回日本。
一些中国僧人也东渡日本传播佛法,同样带去了不少佛像、经书,最知名的当属鉴真和尚。他在日本负责传律受戒,统领日本僧佛事务,并在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根据记载,他在东渡时带去了如来、观世音等佛像八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七种,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
(2)宋元明时期
从宋朝起中日之间虽然停止了官方使团的互派,但两地频繁往来的贸易,以及大量日本僧人前往中国寻访圣迹,让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继续活跃着。这段时间里,由于两国人民的审美趣味不一,那些流入日本的日常用品、手工艺品、绘画作品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文物收藏的重要补充部分。
这个现象以中国书画最为典型。当时中国流行两种绘画风格:一种是华丽细腻、刻画严谨的院体画,以北宋宋徽宗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从宋朝逐渐兴起、至元明兴盛的文人画,他们注重笔法,讲求抒发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描绘内心的精神世界。
但是那些在中国的日本人购置的中国书画和上面提到的这两种虽有重叠,但也有差异。他们大部分人是居住在浙江地区寺院里的佛教僧人,更加青睐宗教性质的道释画,主要为佛教题材的人物画像、著名禅师的肖像画等等;此外,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一些花鸟画。
宋朝禅宗传入日本,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崇尚粗放空灵之美的风潮,而当时中国正有一类被称为禅画的作品符合这种审美。它们脱离了传统的笔法程式,用一种更加自由的笔墨进行创作,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禅画家当属宋末元初的牧溪。
在中国画坛,牧溪并未受到重视,甚至有评论家批评他的画“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但是日本古籍《松斋梅谱》认为“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装缀”,分外推崇,甚至可以说牧溪是对日本绘画影响最大的中国画家之一。现存作品大多收藏在日本,代表作《观音猿鹤图》是京都大德寺的镇寺之宝。
此外,宋朝饮茶的风气也在此时传入日本,随之流传的还有福建地区建阳窑生产的建盏。墨黑的釉底上分布着星星点点的斑纹,纹路有兔毫状、油滴纹、曜变纹等。由于日本人太过喜爱这种瓷器,很多时候不舍得拿来喝茶,只是供放起来作为赏玩之用,因此保存了下来。国内随着明代建阳窑停产,现在存世的建盏已经很少了,而且精美程度远不及日本的藏品。
(3)近现代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贵族和官员将家中收藏的大批文物书画拿出来寄卖,甚至清末民初皇室也会将历代帝王的收藏出售、抵押,再加上当时民间大规模的非法盗掘、侵略者强行掠夺,这个时期成为历史上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高潮。这些文物不仅流失到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很多也进入了邻国日本。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就曾经记述过,1925年他将带出宫外的部分书画、珍宝抵押给当时的中国盐业银行。这批抵押品后来在北京被拍卖,当时日本最大的文物公司山中商会就曾趁机购进一批顶级官窑瓷器,之后转运到日本展览并拍卖。
1902年至1914年短短12年间,日本大谷探险队三次前往包括新疆、甘肃在内的中亚地区,盗窃、购买了不少经本、壁画、彩塑。
此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时期,出现了一批因实业发家致富的企业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他们购置古董创造了经济条件。之后,不少藏家将自己的收藏捐赠给博物馆或者干脆创建私人博物馆,比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部分文物来自收藏家横河民辅、古董商广田松繁的捐赠,安宅英一丰富了大阪东洋陶瓷博物馆的收藏,根津博物馆和泉屋博古馆的藏品分别以根津嘉一郎和住友吉左卫门及其家族的收藏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又一次对我国进行了疯狂的文物洗劫。据统计,大约多达10万件珍贵文物在战争期间流失日本,其中包括现在依然下落不明的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
这些流落在东洋的文物,除了一部分进入了日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一些在近现代辗转至美国,比如我们之前在文章《当为<国家宝藏>疯狂打Call时,也请不要忘记这些没能“回家”的中国文物(北美篇)》中提到的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就是通过京都大德寺辗转进入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中的。此外,也有部分文物在近些年通过拍卖等艺术品交易途经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在日本博物馆感受中国风
由于日本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和机构众多,再加上篇幅有限,我们在这里仅挑出了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
(1)東京国立博物館
城市:东京 亮点:最重要的海外中国文物收藏之一
作为日本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不仅拥有优秀的日本藏品,中国藏品也是数量众多,并且不乏精品。
展品门类丰富,涉及玉器、青铜器、佛像、绘画和书法作品、墓葬文物、漆器、纺织等手工艺品等。在87件日本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中,分别有11件和146件中国文物入选,因此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成为拥有最重要的中国文物收藏的海外博物馆之一。
以中国书画为例,馆内收藏包括了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李迪《红白芙蓉图》、传为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等中国美术史教科书中一定会出现的作品。
画家梁楷的作品格外齐全,《李白吟行图》、《释迦出山图》、《雪景山水图》等水墨作品均收藏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洒脱放逸与工瑾精细并存。
(2)东大寺正仓院
城市:奈良 亮点:探访已逝的唐代遗风
走进奈良正仓院,仿佛经历了一场时光穿越之旅,回到了大唐盛世。《正仓院考古记》的作者傅芸子曾经感叹:“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
正仓院是日本皇室的宝库之一。圣武天皇驾崩后,光明皇后将他生前的日常用品和收藏品交给东大寺保管,寺院将遗物收入正仓院。藏品多与唐代有关:有些是直接从唐朝带回的中国器物和艺术品,有些是日本仿照中国器物制造而成的,还有部分是从中国间接带回的西域器物。
藏品种类包括了家具、乐器、兵器、服饰、佛教造像等,包罗万象,数量达到一万件左右,不少可以和同一时代的佛窟、墓葬壁画相互印证,生动展现了唐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初这些收藏是不对外公开的,后来少数有资格的人趁着寺院每年秋天曝晾文物之际入内观赏。今天,正仓院还保持着这个传统,平时宝库关闭,仅在11月前后举办短暂的售票展览,轮换展出仓库中收藏的文物。
地址:奈良市雑司町406-1 官网:shosoin.kunaicho.go.jp
(3)泉屋博古馆
城市:京都 亮点:青铜器精品
住友泉屋博古馆在中国之所以大名鼎鼎,是因为其出色的青铜器收藏。除了夔纹鼓、鸱鸮卣、鸱鸮尊等珍贵的青铜器以外,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虎卣可谓是镇馆之宝,据说在世界上仅存两件,另一件收藏于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因为虎口中含着人头,之前它被称为“虎食人卣”,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解读也众说纷纭起来,有学者将之解读为“人类通过虎与神明沟通”、“周朝宣称具有护卫天极的资格”等。
泉屋博古馆中的中国书画收藏也十分精彩,传说出自南宋画家阎次平之手的《秋野牧牛图》、清代八大山人的《安晚帖》、石涛的《庐山观瀑图》均收藏于此。而日本古代与近现代绘画、书法、茶道用具、文房四宝等也组成了丰富馆藏的一部分。
(4)有邻馆
城市:京都 亮点:宋元明清书画
有邻馆可谓是最任性的、最难参观的博物馆之一了,开放时间极为短暂,每个月仅第一个和第三个周日11:00-16:00开放,旅行者需要提前特别安排行程才可赶上。但是对于爱好中国艺术的旅行者来说,面对丰富、高质量的中国书画、青铜器、佛像等藏品,这些大费周章似乎也不值一提了。
有邻馆创始人藤井善助曾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留学,后成为近江商人,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其间收藏了大量中国书画、器物。黄庭坚的《李太白忆旧游诗》、许道宁的《秋山萧寺图》、王庭筠的《幽竹枯槎图》、陈洪绶的《花鸟图》、郎世宁的《春郊阅骏图》等大名鼎鼎的作品均可以在这里欣赏到。
(5)日本其他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机构
参考书籍:
《谁在收藏中国》,作者卡尔·迈耶、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作者王晓秋 《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作者富田升,赵秀敏译
欢迎关注:
穷游锦囊微信公众号:qyerguide
知乎机构号:@穷游锦囊
下载有用、有趣、能救命的 “穷游锦囊APP”,获取全新的旅行灵感及实用的旅行指南。